风,是大自然谱写出的灵魂狂想曲,是万千世界中最不被定义的壮烈诗歌,它可以是翻卷出惊涛骇浪的元凶,可以是摧云集雨的祸首,但也可以是传播花种与希望的仙子,可以是散发出童真和快乐的天使。青春也是如此,不被评论,不被定义。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是苏学士笔下的风。在他笔下,风是不惧衰老,不惧谗言讥讽的豁达。苏轼一生漂泊于深不见底的权斗,从反新法到乌台诗案,再到四处漂泊贬谪的后半生,伴随他的风本应愁苦忧伤,却被他提笔一点,成了载千帆过的“快哉风”。即便面对夹杂大雨的狂风,他也能“何妨吟啸且徐行”;就算面对衰朽残年的弱风,他仍能“左牵黄,右擎苍”以内心化风“千骑卷平冈”。
“纵有狂风平地起,我亦乘风破万里。”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两弹元勋、核潜艇元勋等国之脊梁心中的风。在他们心中,风即便狂妄,声势浩大,也不过是“乌蒙磅礴走泥丸”。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国家研制核武器只能依靠算盘、稿纸和粉笔,苏联几乎撤走了所有援助,美国总统也声称:“只要自己还活着,中国就不可能造出原子弹和核潜艇。”可就算狂风肆意,先辈们也未曾放弃,他们隐姓埋名,兀兀穷年,潜心研究,天命终不负有心人,1964年天空上的那一朵蘑菇云,就是冲出这狂风的最好证明。
“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这是我心中那首独一无二、不被定义的灵魂独唱。微风吹动少年人的衣角,掀起的是一整片自由辽阔的草原。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的风可以是飘零轻狂的年少肝胆,也可以是平凡清晨那最不惹眼的微风,正如我,可以是振翅雄鹰,也可以是亘古绿树。
没有人可以规定风吹的方向,也没有人可以界定青春的畅想,与我奔跑的风永不被定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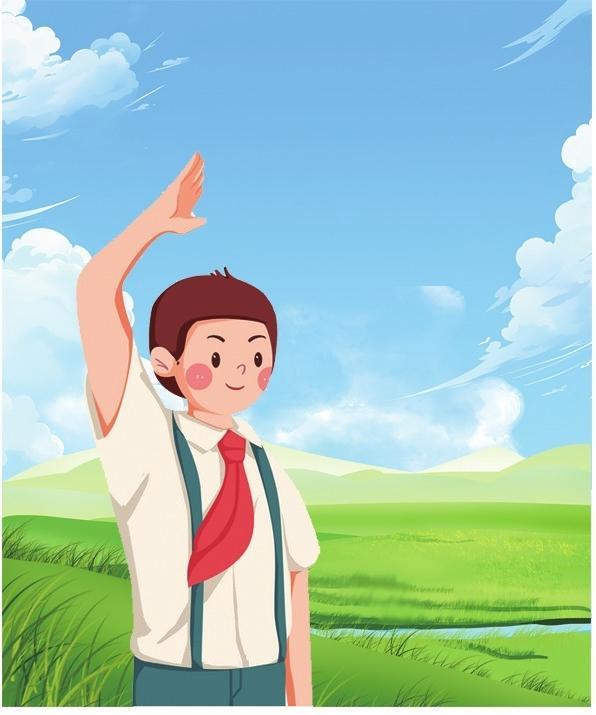
 甘公网安备 62010202002336号
甘公网安备 620102020023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