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佳节通常都是阖家团聚的时刻。但古往今来,出门在外由于各种原因在他乡过年亦为常态。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甘肃是谪官戍边的必经之地;而一些外国探险家或学者游历中国西北时往往也在甘肃长期驻留。近代游记史料中,不乏失意官员和老外在甘肃特别是在兰州过年的记录。他们的甘肃春节记忆是怎样的历史图景呢?
一
裴景福(1854年—1926年),字伯谦,安徽霍邱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授户部主事,后长期在广东为官,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谪戍新疆。同年冬行经兰州并停留数月之久,其日记后汇编为《河海昆仑录》,留下了120年前兰州春节民俗的珍贵史料。
那一年的兰州春节堪称暖冬,裴景福日记中的每日气候不是天晴就是不甚冷,偶尔微雪。好天气可能使其贬谪途中的灰暗心情颇为好转,于是入乡随俗安心在兰州过年。1905年腊月二十九,他向老家发电报报平安,告知家人要留兰州辞旧迎新。大年三十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安排仆从办年货,“过年食物量为买办”。身为收藏家的裴景福在兰州寓居期间已经在金城古玩界小有名气,除夕午后古玩店主老刘持《醴泉铭》(即《九成宫醴泉铭》,唐魏征文、欧阳询书丹)拓片拜访裴景福求售,“阅之北宋拓也,惜残失二十余字,墨色昏黯。以十金得之。”“重出八九字,亦宋拓也,若重装背,得一二名手,为之题跋,百金以上物也。”由此可见,清末兰州古玩行每逢春节主动拜访官宦之家上门推销文物俨然成为行规抑或一种营销策略。
裴景福购得这批文物后,当即与一众同年和同乡赏玩,“惊为至宝”。到了年三十晚上,“远近爆竹不绝。兀坐一室,焚香扫地,煮佳茗,取书画静对澄观,极人间萧闲之致。”裴老哥这是准备一个人清心明志独自过年吗?非也!据其日记自述,一边欣赏书画一边回忆起在广东做官时过年如何热闹,现在贬谪新疆途中流寓兰州,门前冷落鞍马稀,于是祭出精神胜利法:“今年胸中空阔,别无挂碍,人不来我亦不往,甚自得也。”晚清官员贬谪,沿途官场多少要给几分面子,特别是为官之同乡亦多有照拂。裴老哥刚做完自我心理调适,几位寓兰同乡就专门前来陪他辞岁,“做菜五六品,食之颇甘,举杯徐饮畅谈,不觉带醉。”随后他又体验了兰州民间正月初一凌晨赴寺庙道观上香的习俗,“夜半诣许真君殿上拈香”。回到下榻处睡不着觉,“归作家书”,一边写信一边“渴甚思饮”,酒后口干舌燥不禁感慨兰州的白酒就是够劲:“酒犹兵也,兵犹火也,止酒固宜”。折腾到凌晨快三点才睡觉,“丑未始就枕”。
正月初一,“天气晴和,午后更暖”。裴景福上街转了一圈,“市间甚为清淡,闻合省官僚诣督辕贺年,升帅(即允升)在二堂受礼答拜。各司道即就督辕大堂与僚属群见互拜。传谕勿再到署,以省虚文。”这就是今天的政府机关团拜会了,裴景福据此认为:“凡实心行实政者,外面浮文去一层,则向里面进一层。上下情意自然洽惬。”正月初二上午有三五
知交拜年,下午他则干了一件风雅事:“今日得黄河水,取柳枝,烹以铜铫……于风沙冰雪中思之,如登仙矣。”
正月初九,“是日甘省迎春,红男绿女,喧闹衢市”。正月十二,时任甘肃提学使杨增新组织酒局,裴景福应邀赴宴,“至则金貂满堂,甘省提镇统兵将领俱在”,与众人酬酢甚欢,菜品中“以烤羊肉和清炖鸭尤美”,可见烤羊肉在兰州这座碳水肉食之都的统治地位古已有之,而且能登大雅之堂。裴老哥归途经大南门,“春灯照耀,明月无光”,兴之所至,索性又到同乡家中小饮,杀了个后场。正月十五,省城主要官员齐至兰州东校场行迎喜神礼;入夜,“月明无织翳,万灯齐明,游人足跷而踵相随,车骑连伍而行。”兰州元宵灯会官民同乐,裴氏感慨“真太平景象也”。
二
马文·韦勒(1900年—1976年),美国地质学家,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20年,退休后任该校沃克古生物博物馆馆长。应中国政府邀请,他和另一位美国地质学家弗雷德·萨顿及中国地质学家孙健初于1937年6月抵达兰州,随后在甘肃和青海相关地区开展地质调查和石油勘探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夕,他们从河西走廊返回兰州,一边整理调查资料一边等待局势变化,同时体验了甘肃百姓在战火中如何辞旧迎新。
据其所著《戈壁驼队》一书记载,1938年1月9日(农历腊八),兰州教会医院的韩大夫可能觉得用一碗“腊八粥”不足以表达对美国友人的盛情,于是安排了一顿鸡汤火锅。开胃小菜是脆黄瓜和果酱,料碗是芝麻酱,涮菜以羊肉片、鸡肉片、豆腐、白菜心及其他蔬菜为主,主食有拉条子和芝麻烧饼。两位美国老哥认为饭菜好极了但确实吃不下这么多。次日他们又去城隍庙散步,零距离接触了市井烟火。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
年,彼时虽然兰州已经遭受日机轰炸,但战争阴影之下的金城百姓仍然保持了乐观平和的心态,隍庙里头年味渐浓,刮碗子和娱乐活动正常进行,“一伙一伙的人围着小桌子在喝茶吃东西,几个琴师和卖唱的则到各个桌前演唱讨几个赏钱。有一个盲人拉一把很大的二弦琴(即二胡),还有一个木制响板安在一个架子上,盲人一边拉琴一边用脚踏动响板,这效果有点像中国的爵士音乐。”
离开兰州前夕,朋友们按当地风俗以蒸饺和油炸饺子为他们饯行。从腊月十一晚上开始直至抵达西安,他们切身体验了战争对于旅行者带来的影响,更看到了甘肃百姓全力支持抗战的坚强意志。途经华家岭时,他们目睹了西兰公路铺设碎石路面的场景,石头要从很远的地方翻越陡峭的山路运到施工现场,采用了各种运输方式,包括骡车、牛车、牲口驮运甚至人背,令他们深受震撼。在定西住宿时,他们全体挤在两间小屋里,“除了炕和纸糊的小窗户以外,什么都没有”。晚上气候十分寒冷且没有晚饭供应,中方人员自行外出觅食,两位美国老哥只好开了一听罐头、在炭火盆上煎两个鸡蛋,用这样的“野战食品”勉强果腹。在静宁和平凉住宿期间,众人不得不全身裹着毛毯、棉被和皮大衣抵御腊月严寒,所幸沿途那些“带有店铺红色印章”的糖烧饼、油炸麻花和馒头等甘肃特色小吃为他们提供了不少舌尖上的慰藉。
最后要提及的是美国人华尔纳(1881—1955)和美国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一次中国考察团的甘肃之行。1924年2月初,他们自敦煌盗宝返回兰州期间度过了一个百味杂陈的中国春节。华尔纳所著《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一书里,对此不乏做贼心虚式的心理描写:“虽然我紧张不安,担心马车前部放的箱子里面的那尊珍贵雕塑会受到损伤……在酷寒逼人的二月之夜里,几个小镇上都悬挂着红灯,人们正忙于庆贺新春的到来,而我们却连住处和食物都没有。”20世纪20年代初,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甘肃人民开始以这样的“不合作”方式对待外国文化强盗。当他们停驻肃州时,当局又收缴了华尔纳从金塔县寺庙盗取的青铜佛像一尊。好不容易熬到年尾巴——按时间推算应该是正月二十几,华尔纳在兰州时又被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上了一课:“(安特生)很舒适地住在一座大宅院里,那是他的冬季用房,一会儿,我们便就一些专业话题深谈起来。我一边啜泣饮着他的杜松子酒,一边鉴赏他那些不寻常的考古发掘品。”华尔纳在兰州花了整整四天时间聆听安特生的谈话,“仿佛久渴的人啜饮甘露一样”“这儿成为我在独自去北京的一个月艰难路途上思考无尽的地方”。
华尔纳考察团的甘肃春节记忆,用他自己的视角来说,前半段处处感受到甘肃官民的敌意,后半段又被安特生的科学考察成果所震撼,顿感自己的盗宝行为与正规科考相比简直不入流,不禁自惭形秽。而马文·韦勒等人的甘肃春节记忆,不仅体现了他们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战,而且保留了全面抗战爆发之初甘肃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和坚信抗战必胜的精神面貌。两段老外笔下的甘肃春节记忆相差十四年,对于当事人来说同样刻骨铭心,但其气量格局和历史意义高下立分,不可同日而语。
撰文/史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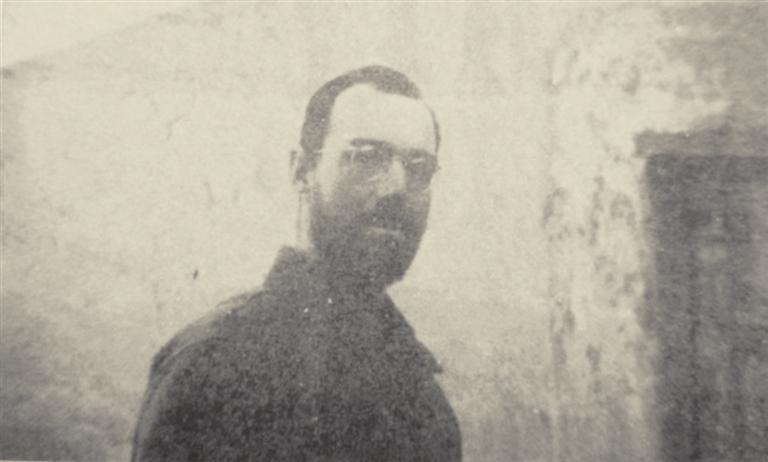
 甘公网安备 62010202002336号
甘公网安备 6201020200233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