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题记
夏尽秋初,褪去青涩的绿,徒留枯败的叶,但,留得残荷听雨声,我在雨中等再春。烟水弥漫,雨落青瓦。夏浓烈时,绿荷如青壑。本是些惊不起波澜的残景,却由诗词盖上一层迷蒙的神秘。
“映日荷花别样红。”似是有很大的区别,被赋予了不同的感情色彩,这不正是语文之美?
诗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总是以“诗词的民族”自居,可我们的时代从来不是一个诗词的时代。手握动车票,故乡的桃花是否开放也无关紧要;车水马龙的城市,一轮残缺的月亮,也成了无关紧要的话题。
时代的步履太过匆忙,人类创造着新世界,同时也在消解着原来的世界。
如果天涯海角被拉为咫尺,那么遥寄相思是否还有意义?
如果风花雪月被化作规律,那么造化神化是否还是瑰丽?
如果喜怒哀乐都得以解释,那么那些抒情言志是否还有作用?
时间的长河中,我清晰地看到古人们站在上游,咏叹着万物。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我看见一抹青荇,漂在我的面前,在清波中摇晃。然后……
满船清梦压星河……夜深千帐灯……暮霭沉沉楚天阔……春青河畔草……
终于汇聚成一条绵延万里的历史长河。
光芒透过文字的缝隙,折射出另一个世界。
彼时,他站在洞庭湖边,咏赞着大自然的伟大……
彼时,他在秋水长天,看着落霞与孤鹜……
彼时,他身着白衣,载着酒壶仗剑天涯……
彼时,她载着晚舟,误入藕花深处……
彼时,他靠着墙壁叹息,憎叹战乱带来的不幸,颈间的白发垂落在地……
彼时,他,她,他们透过玻璃窗,与我站在同一时空。“这不正是诗词吗?”顺着他们的目光看去,窗外,城市正泛起黄昏,高楼间的灯光,正一一亮起。
是啊,我们站在同一轮月光下,用眼睛眺望着同样的大地,诗词怎么会离我们远去?
我们仍如亘古以前的先民,稚拙却虔诚地发下第一个音节,刻下第一个字符,渴望与从前共鸣。
在这一刻,我们并不能让飞速运转的城市停滞,但我们可在寻常中寻一份安逸,在嘈杂中寻觅心灵的共鸣。
好在有诗词,即使我们与亲人相隔千里,每当我们共同抬起头望明月,就会知道有人在挂念,知道“月是故乡明”。知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好在有诗词,即使是无边的雨景烟垣,也能从中寻觅几分乐趣。“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
好在有诗词,让我们心中那些仗剑行江湖的梦,在诗词佳句中找到知音。
好在有诗词,我们知道一切虚妄之间,总有些东西高于其他。
好在有诗词,我们还记得,相隔的从来不只有空间距离,还记得风花雪月从来不只是规律无情,还记得喜怒哀乐从来不能简单概述。并且记得,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特殊。又或者,人类的文明,需要某样富有情感色彩的文学传递下去,譬如:诗词。
因为诗词,我才更愿意沉浸于语文之中,感受人们的喜怒哀乐,分析人物的色彩。
诗词,让我安心做一个光阴百代里,最平凡的过客。
诗词,让我寻觅语文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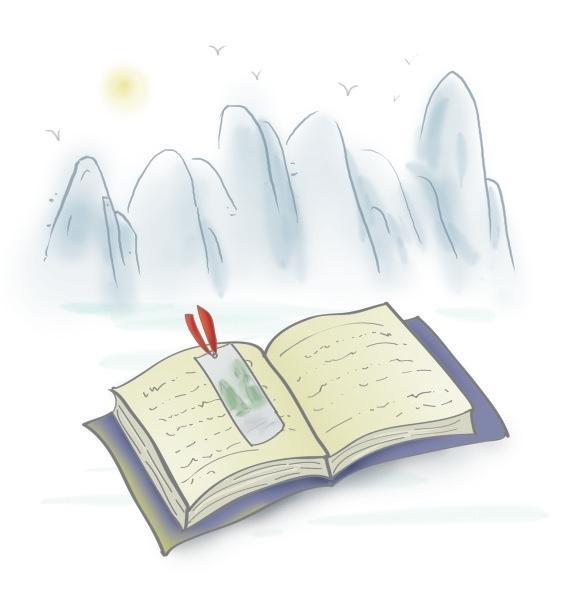
 甘公网安备 62010202002336号
甘公网安备 62010202002336号